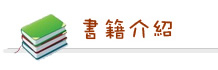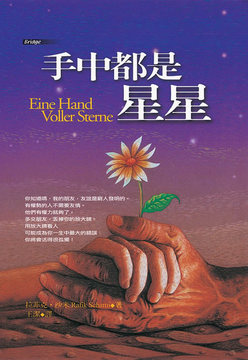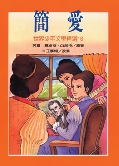日記如拼圖,拼湊一個陌生且奇妙的世界
◆林倩葦(兒童文學工作者)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曾寫過日記,不管是為交差而寫出來的流水帳式的紀錄、或為抒發個人內心情感與志向而編織的秘密字語。但絕少數人會像作家拉菲克.沙米(Rafik Schami)把日記當拼圖,為讀者拼湊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少年故事。
《手中都是星星》是一個麵包師的兒子所寫的日記,讀者透過他的眼睛看到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五O年代的情景、認識一位少年的故事。故事的情節圍繞在這位少年的學校、他的戀人以及他對記者工作 -- 一種在這個國家中屬於非常危險的職業 -- 所萌發的興趣。故事首先由這位不具名的少年以第一人稱在日記中描述他身為麵包師兒子的生活,讓讀者在故事開端嗅到一絲絲少年的幼稚,隨後這種無拘束的敘述語調帶領我們進入這位少年在大馬士革的家庭、學校、社區、認識他的朋友和當地的政經狀況等。這本日記小說從第一年的一月十二日跨越至第四年的七月十四日,作者時而以插曲方式、時而利用焦點觀察,將這些片斷的日記編織成一幅完整的圖像,讓讀者見證了主角從十四歲到十七歲的(生理與心理的)成長過程、與好友老馬車夫沙林的友誼、和記者哈比比的交往與學習、以及對記者工作的熱情與執著。
書中的主軸乃少年與沙林伯伯之間的友誼,從沙林伯伯鼓勵少年寫日記、適時的阻止他離家出走、對他的志向與生命的啟發、直到沙林伯伯病逝為止,作者在數則日記中非常細膩的刻畫兩人的互動與情感。這份友誼帶有教育性的意涵,卻沒有階級式的關係。本書中文譯名《手中都是星星》非常貼切原德文書名 “Eine Hand voller Sterne”,這裡的手可隱喻為沙林伯伯的手,手中的星星代表希望,在主角悲傷的時候,他的手帶領他通往希望之路,就像星光照亮黑暗的夜空一樣。而少年與記者哈比比的情誼則是另一個重要焦點,就許多層面來看,哈比比具有反派角色的意味,讀者從這個人物身上看到對抗國家統治系統的地下政治活動。哈比比也扮演少年的導師,但和沙林伯伯不同的是,他的態度是有距離、防衛性的,一直到少年對記者工作的熱情與專業有了進展後,這種拒人於千里的態度才漸漸消散。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市井小民、或學校裡的老師、或傳教士、或瘋子、或記者、或政治人物,作者對各種角色的語言拿捏得恰到好處,讓語言本身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深深的感動讀者。
對作者拉菲克.沙米的背景頗有瞭解的讀者很容易將這本書認定是他的自傳體小說,因為沙米雖用德文寫作數十年,但本身來自敘利亞、在大馬士革度過童年、他的父親是麵包師傅、他曾在父親的麵包店裡工作、自己所熱愛的卻是寫詩或幫遊客作導覽、而且他確實有位忘年之交 -- 擅長說故事的老馬車夫沙林。沙米在2002年五月初所寫的〈談寫日記與待寫的人物〉(Vom Tagebuchschreiben und von wartenden Figuren)文中曾提到,他一直(在911事件之前)未曾嚴肅的寫過日記。出於好奇,他很喜歡閱讀他人出版的日記,但自己在兒童或青少年時期都不曾寫過,因為他不確定自己想寫的是否真的要長久保密。在他小時候的大馬士革家中,擠滿了五個好奇的兄弟姊妹和許多親朋好友,家裡隨時像一座客滿的火車站,根本沒有一處自己專屬的角落。而吃飯的情景更熱鬧有趣,因為經常有不請自來的親戚甚至陌生人和他們一起共餐。秘密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就連在教堂裡對神父作的告白一樣也藏不住;他在告白時都得講些無傷大雅的瑣事,否則患有重聽的神父會將他的罪狀大聲的重述一遍,讓等候告白的人聽到,日後成為大馬士革舊城區所有居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另一個沒想要寫日記的原因,可能是沙米從小就喜歡說話,習慣以說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沒有特殊動機需要藉助沈默的日記抒發情感。沙米在文中坦承,《手中都是星星》這本書他一開始用不同的形式下筆,例如第一人稱、第三人稱、或書信體等等。然而每完成一個故事老覺得有些地方怪怪的,直到選擇以日記的方式來呈現,成功的去除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讓語言的表現更生動且直接,並且把這本日記體小說提升轉化成藝術之作。
不論書中的情節與作者的童年經驗有幾分真實之處,這本日記體小說的確如拼圖般,為讀者拼湊一個陌生、有趣的世界,讓他們有機會窺探在離我們那麼遙遠的、不同國度與文化中的一個少年的成長心情與故事,故事結尾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我們不知道少年的未來是吉或凶,然而我們確信,不管未來的道路如何崎嶇,少年將會稟著對生命的熱情,繼續往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