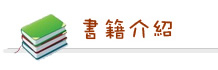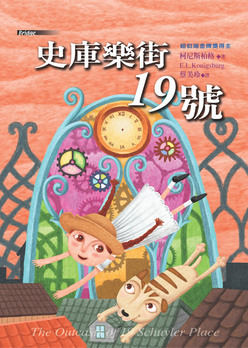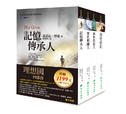這本書的主角瑪格列特‧露絲‧凱恩是《沉默到頂》(Silent to the Bone)康諾‧凱恩的同父異母姊姊。它敘述瑪格列特十二歲那年暑假的經歷。故事由塔里夸夏令營講起,她在那個夏令營裡,被幾個同住一間木屋、原本就是一夥的室友惡意作弄,還替她取了不堪入耳的綽號。氣憤之餘,她也採取「不合作」運動,不參加戶外健行、不參加湖上戲水,卻因此被貶損為「無藥可救」。害她的夏令營日子悽慘難過。幸好在還沒被摧毀之前,她的兩位舅公──艾力山達、還有莫里斯──將她救出了夏令營。 平安返回舅公位於「史庫樂街十九號」的住家時,她才發現原來她的舅公也正需要救援。過去四十五年時間,兩位舅公在住家後院一點一滴建造三座高塔。由於受到少數強勢住家所有權人的壓力,三塔被宣告為「街坊之害」,市議會投票決定,擇期拆除。瑪格列特‧露絲覺得三塔根本是無可取代的藝術品:三塔會唱歌,會發出喜悅之音,它不僅是巨大完美的象徵,也是歷史的頌揚。瑪格列特‧露絲決心讓它們永遠唱下去。 從無與倫比的柯尼斯柏格筆下產生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它是一個關於藝術、歷史與竭力保護個體存在的故事。
傑克和我一起坐在屋後的階梯上。我們看著三座塔,就只是看著,看了好久,然後我說:「我爸媽去祕魯這段期間,我就是想待在這裡。」
傑克回答:「我能了解。我也會想待在這兒。」
那個時節輪到燈籠形的「大腹椒」結實。沉甸甸的果實把莖幹壓彎,垂得低低的。「莫舅公種椒,」我說:「艾舅公種玫瑰。」
「那三座塔呢?誰建造的?」
「兩個人都有。他們不停的蓋,已經四十五年了。這三座塔比我媽媽年紀還大。」
我指著「塔三」與柵欄間的鋸齒形空地:「那兒還有建造第四座塔的空間。」傑克舉手擋光,瞇眼順著我指的方向看去。「新塔要細長型的,才放得下。」他細看那個地方,在腦海中想像著那座塔。「很多零件做好了,放在地下室的工作間。」
傑克的目光上下移動,再緩緩橫掃,視線始終沒有離開三座塔,一秒也沒有。他兩肘擱大腿上,兩手合攏,像在祈禱。然後他定睛在離後廊階梯最近的那座塔。「那些吊飾,誰做的呢?」
「都是艾舅公做的。他用砂輪磨出每一片的形狀,用鑽子鑽洞,再穿進銅線。莫舅公負責在塔的支桿上鑽洞,好掛銅線。他們做工作的時候不是用討論的,而是一直吵。每一片吊飾都要吵。要是莫舅公問:『洞要鑽在這兒?』他用手指著。艾舅公就後退,斜眼著看莫舅公手指的地方,然後說:『不對,是這兒。』一邊指著距離莫舅說的那位置半公分的地方。莫舅公就說:『你要鑽這兒?』艾舅公說:『我剛才不是說了嗎?』莫舅公說:『你確定?洞一鑽下去,我就沒辦法讓它消失囉。』然後艾舅公又退後,看看,說:『要是你那麼不確定,我要再想想看。』『我沒有不確定,不確定的人是你。』莫舅公兩手往上一甩,說:『Jaj, Istenem!』意思是:噢,老天!那是他經常掛在嘴上的話。打從我認識他們起──也就是我這輩子──他們就住在一起,也一直吵到現在。我媽說,看他們掛吊飾,花一張歌劇的票價也划算。她很愛那三座塔,我也是。」
「只有死人才會不愛。」他說。
「那就是我爸爸嘍。」我說。
傑克很難為情。「我的意思不是……」
「沒關係,」我說:「我爸爸和兩位舅公本來就不合。」
我爸爸認為,蓋了三座有鐘面卻不報時的鐘塔,是一種浪費。這年暑假我沒到舅公家過,舅公也沒來吵這件事,害我難過得要命,爸爸卻開心得要命。爸爸擔心要是我與兩位舅公住上四星期,就會永遠忘了離開房間要關燈,也永遠不會守時。他抱怨兩位舅公不但亂丟鑰匙、亂丟帳單,更亂花時間。特別是時間。爸爸信的教,大概叫做守時教。
我爸爸說到時間,是把它當成一種信念(譯注:原字同時指受胎之意)。而我知道的「受胎」的唯一定義,是指他當了某樣東西的爸爸。他,是我的爸爸;他,同時也是「時間老爸」。浪費時間他也擔心、時間不夠他也擔心。他最常操心的是失去時間。小時候,我總以為,有一天我可能會在牛奶盒上看到他為尋找失蹤的「時間小孩」而登的照片。對爸爸而言,時間是要讓人去節省的。他老在節省時間,卻從未提到,省下來的時間,都拿去做了什麼;也不曾有人因此質問他,因為一般人只會讚佩節省時間的人。
對兩位舅公而言,時間是給人花用的。
碰到有人問我爸爸對三塔的想法時──我最恨那種時候──他會說,三塔不僅「無用、多餘、極度浪費時間」,還「過分浪費金錢」。
我媽媽的態度是:「過分?沒錯,那三塔是過分,卻不見得浪費金錢。偶爾一個人是可以單純的去做他想做,也覺得值得做的事,這樣並不會使那件事變得沒有價值或者浪費時間。的確,那三塔沒有實際功用,它們不遮蔭──「大衛像」也不遮蔭;它們不用來架電話線──艾菲爾鐵塔也不用來架電話線;聖母院的玫瑰圓窗透進來的陽光,微弱得讓人連字都看不清。不過根據我的定義,聖母院的玫瑰圓窗可沒有因此而變成無用或多餘。三塔矗立在那兒,純綷因為建造它們是值得的。沒有它們,我的世界就沒這麼美、也少了很多趣味。」
每一個人都是故事! 鄧美玲(上善人文基金會執行長)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在台北縣某一國小的《論語》教學實驗課程,剛好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四年級的孩子聯手作弊。
作弊當然要處罰。這是學校教育的普遍思維。但是,怎麼罰才不是只有「罰」,而可以帶著「學習」的意義?最重要的是,如何藉由這個事件,幫助孩子作價值觀的釐清?
我們的討論從作弊是為了得高分開始。小朋友想要得高分,基本上都是受到爸媽的影響,考好了有獎品、考壞了會挨罵。而爸媽因為愛,想要孩子「好,還要更好」,但又說不清楚到底怎樣才是「更好」;於是,「好成績」等於「好學校」等於「高成就」,而這個等式也被社會大眾簡化成幸福成功的指標。這些都是人的「基本社會慾望」,就像吃飯、喝水一樣,是維持生存的本能。但慾望的發展又會演變成各種面貌,於是,價值觀就慢慢形成了。
小學四年級孩子的人格發展特質,已經可以引導他們逐漸了解:價值觀的形成,受到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例如個性、家庭教育、社會環境、流行文化等。一個人倘若不受流俗影響,敢於堅持己見,這又可能發展成兩種極端:一是反社會行為,一是自命清高。如何選擇適當的行為,從「不委屈自己,不為難別人」開始,學習保持和諧的群我關係?這個能力的養成,應該是所有學校課程的核心價值。譬如,最近我在台北縣頂溪國小王修亮老師團隊的教室裡,看到她們紮紮實實的都做到了;而我也正在向她們學習,並思考如何深耕教育的可能途徑。
因此,在讀這個故事時,我不時退出來思考:如果要借這本書當作課程,它可以放在整個教學脈絡的哪個位置上?
十二歲的女孩瑪格列特‧露絲‧凱恩被忙碌的父母送到夏令營,在那裡受到同寢室女孩的聯手欺負。於是她開始採取溫和的堅決反抗,最後逼得夏令營負責人只好讓她的舅公來把她領回去。不過這只是序曲。這種反抗的意識,促成她後來展開爭取保護三塔的行動。三塔是兩位舅公花了四十五年時間,利用金屬、玻璃與瓷器碎片,慢慢在自家後院建造完成的。因為街區開發,三塔遭到強制拆除的命運。瑪格列特透過各種關係,甚至讓當初欺負她的女孩們也加入行動,終於成功搶救三塔。
有趣的是,這個出自紐伯瑞金牌獎得主柯尼斯柏格之手的故事,是從她另一本作品《沉默到頂》(《Silent to the Bone》)旁生出來的。她自己在「致讀者書」裡提到:「我寫完《沉默到頂》那本書之後,康諾‧凱恩的同父異母姊姊,瑪格列特‧露絲‧凱恩不肯離開我。其實那時候,我也不肯離開她。我一直思索著瑪格列特那段回憶:『十二歲那年,我從夏令營返家。……記得,下樓晚餐時……理解到,我們這個家,永遠不會再像往昔了。』我曉得瑪格列特在夏令營裡過得很悽慘。」
一個故事裡的配角,換一個角度,就是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每一個人的行為背後,都有綿密錯綜的肌理網絡。這本書的故事最後,經過轟轟烈烈的搶救三塔行動之後,回到現實生活,瑪格列特一樣遭遇很多困難,例如:爸爸的外遇,以及隨之而至的爸媽離婚,接著是兩位愛她的舅公先後去世。而在《沉默到頂》這本書裡,她長大了,把舅公留給她的老房子改成辦公室兼住家,經營電腦顧問的事業。這就是真實人生。
這是多麼好的課程素材啊!
如果能帶孩子用這種眼光讀這本書,書中每個角色都可以自成一個故事——營區主任柯普藍太太、裝傻的傑克、「野雲雀」小木屋裡那幾個耍陰險欺負人的女孩子……我想像著老師們若能引導孩子各自選擇一個角色,用自己的經驗,讓故事繼續發展擴大,那麼,我們要幫助孩子學習調和親子關係、同儕關係,乃至「個人的完整性」跟「團體意志」之間的衝突,就有了很好的介面。想想看,一個自信不足、為了贏得友誼,只能依附在團體當中跟著起鬨鬧事的孩子,會用怎樣的故事情節安排「野雲雀」那些「校友幫」的互動?這樣的孩子在學校裡通常不會太惹人注意,但他的人格特質若未能經過適當的引導,長大成人之後,他在社會生活中使弄的小奸小惡,就會給大家添很多的麻煩。而若有小學老師可以及早敏感到孩子的這種特質,又能透過課程引導,很多個性沉痾造成的人生悲劇,至少可以防患於未然。
這種人性改造的希望工程,應該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不過,今天的學校似乎並非如此。然而,這或許也是社會必然存在的侷限!因此,我們除了盡一切努力設法促成外,並不會感到遺憾。在充滿缺憾與侷限的環境中,不論成敗,永遠懷抱希望盡人事之努力,不正是《論語》所開展的生命格調嗎?而我們也正在嘗試透過孩子一個又一個的生活故事,把孩子引到這樣的生命格調中。
★2005年入選ALA年度兒童好書
★2004年SSLI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銀牌獎
★2004入選學校圖書館雜誌年度好書
★2004入選出版人周刊年度好書
★Kirkus年度編輯選書
★華盛頓郵報年度好書
★新聞局推荐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